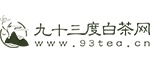- 當前位置
- :
- 九十三度白茶網-福鼎白茶品牌官網-白茶領導品牌
- >
- 茶葉資訊 >
- 正文
- 發布時間:2022-12-06 11:50:50
- 來源:網絡整理
熱點在線丨譚知凡,建水紫陶四老之一
譚知凡,男,建水縣人,1950年2月出生,1973年進入建水工藝美術陶廠工作就與紫陶工藝結下了不解之緣。多年來在從事美術繪畫的同時潛心于工藝美術陶的制作研究。在已故老藝人向福功的藝術熏陶下,在不斷的探索和進取中于1984——1986年到云南藝術學院進行了藝術深造,其思想和藝術造詣日漸成熟,在殘貼、斷卷的傳統工藝基礎上有了新的突破,探索出了陰刻、陽刻一次性完成的新工藝流程,提高了工效,創造了經濟效益。與此同時,與本廠的老師傅何炎華等同志一道大搞生產工藝改革和技術創新,共同首創了紫陶作品制作上的空心刀雕刻工藝,使工作效率猛增至原來的五倍,這一歷史性的貢獻大大促進了工藝美術陶廠生產和經濟的發展。
 (資料圖片)
(資料圖片)
1978年,受全廠和全縣各族人民的重托,光榮參加了“北京人民大會堂更新改造工程”中“大花缸”的制作任務并圓滿完成。使建水各族人民的美好心愿記載入首都史冊。
1983年作品《半幣壺》、《殘貼筆筒》被選送參加全國工藝美術展并被列為珍藏品。
1988年作品《陶藝文具》在省日用陶瓷創作設計評比中榮獲省輕工廳頒發的“創作設計優秀獎”。同年12月由云南省輕工廳、云南省人事廳評定為“助理工藝美術師”。
1993年2月當選為建水縣第六屆政協委員。同年6月,經省輕工廳考核評審,被評為“工藝美術師”。
1995年,在本縣的旅游產品開發活動中,其作品榮獲縣人民政府頒發的“創作設計一等獎”。
2003年,被紅河州文化局、紅河州民族事務委員會命名為“紅河州名族民間優秀美術藝人。”
2007年8月榮獲“云南省工藝美術大師”稱號,同年被評為“高級工藝美術師”。
2007年10月紫陶《扁天球瓶》獲中國創造?民間文化品牌珍貴藝術品”獎。同年12月送云南省首屆“工美杯”精品博覽會獲金獎。
2009年作品《華夏永聯》在第十屆中國工藝美術大師作品國際藝術精品博覽會獲銅獎。
2011年8月作品《般若樽》獲云南省第五屆工美杯金獎。同年12月,被評為云南省第四屆百名拔尖農村鄉土人才。
2013年10月,紫陶作品《六方小方瓶》收藏于李國楨紀念館。
40余年來,為發展紫陶工藝艱苦探索,無怨無悔,在雕刻、繪畫、書法、設計、造型等方面均有了很深的藝術功底,并抱定了為發展紫陶工藝而奮斗終生的決心。成為了聞名遐邇的建水工藝美術陶承先啟后的繼承人。
初次見到云南省工藝美術大師譚知凡,便記憶深刻。這位出生于1950年的建水漢子身材不高,留著"濃密的大絡腮胡,滿臉謙和的笑,深灰色衣褲和黑布鞋沾滿黃土。這滿身的“泥巴味”,使采訪變得輕松愜意。他的作品,獲得過國內各類藝術獎項的許多榮譽。而他卻最喜歡別人稱呼自己為“泥巴匠”。
建水,一座擁有1200年歷史的滇南古城,素有文化名邦美譽。一方水土養一方人,父親是教書先生的譚知凡自幼就對繪畫有著濃厚興趣。1973年,他通過招工進入建水縣工藝美術陶廠。由于有書畫特長,譚知凡被分到美術組,帶他的師傅正是后來被稱為建水紫陶之父的制陶名師向逢春之子--向福功。
能把自己的特長、興趣運用到工作中,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呀!工作后,譚知凡發現,陶器上允許作畫的種類很少,僅有梅、蘭、竹、菊四種。這正是他擅長的。但在陶器上作畫,與在紙上畫畫大為不同,為了讓他盡快上手,師傅教了一個辦法:用一塊玻璃壓在黑布上,自己調制一碗白色泥漿,先在玻璃上練畫,畫完用抹布一擦,反復使用。用這個簡單的方法,譚知凡一邊練畫,一邊在廢陶器上實踐。整整大半年,當他用完一小池子的白泥漿后,才逐漸開始掌握在缸、瓶、罐、汽鍋等各種球狀陶器上布局作畫的竅門。
那年年底,廠里接到了一個出口大訂單,為完成那批汽鍋、花瓶上的梅蘭竹菊裝飾圖,譚知凡每天要畫八九個小時。有一天,畫好梅花之后,心情大好的他又在后面畫了一只小鳥,到了刻填工序,填刻師傅一看,二話不說就去找領導:“你看看,這是個什么東西,雞不雞、鳥不鳥。”在那個年代,超出范圍的事情是不能做的。領導過來發了一通火:“這是政治任務,你畫公雞,難道想把尾巴翹到天上去,畫螃蟹,難道你還要橫著走呀。”從此,譚知凡老老實實畫梅、蘭、竹、菊。
“畫得多了,梅蘭竹菊的形象就刻在了心里。”譚知凡說,隨著陶器生產量越來越越大,畫得越來越多,譚知凡開始應接不暇。為了解決用筆刻畫速度慢的問題,他在老師和工友們的共同啟發下,改良了一個實用的小技巧:從罐頭上剪下一條鐵皮,制作成梅蘭竹菊的特殊形態,再用鐵絲綁成一個錐型,做成一把“刻刀”,這把特殊的刀,只要使順手了,只需手腕輕輕一轉,平刀、立刀、中鋒、細線、側鋒,在各種刀法的信手捏來間,竹葉、花瓣的形態立刻便顯了出來。而且,以刀代筆刻之后,省了一道填泥工序。據悉,這個創造性的技術革新,被當地制陶匠人們沿用至今。
藝術箴言:對工藝美術陶的探究永不停止,每一點收獲都只是一個新的起點。
除了高超的“梅蘭竹菊”陶器畫作,譚知凡還深諳“殘貼”制作。“殘貼”是如今建水紫陶最具藝術技巧的產品形態,傳承人正是譚知凡。走進譚知凡設在自家小樓里的作品展覽室,他最喜愛,擺設最多的也是自己制作的“殘貼”作品。而且,早在1983年,他的作品《殘貼筆筒》就在參加了全國工藝美術展后被列為了國家工藝美術館的珍藏品。
譚知凡說,古時,有一位建水文人先生在庭院里揮筆潑墨,一陣風吹來,宣紙散落一地,先生彎腰撿紙,發現那些一張壓著一張的宣紙露出來的一個個局部疊加在一起后,有一種無可名狀的殘缺美。于是,先生取一書法,截其中一塊,鐫刻到了陶器上,卻意外得到了一種看似殘跡,卻給人無限遐想的意蘊美。從此,“殘貼”成為建水紫陶最特別的藝術形態,制作核心技術一直秘而不宣。
譚知凡的恩師向福功,從父親那里繼承了殘貼手藝,不但熟諳做殘貼之道,還十分開明,希望能將這種藝術形態發揚光大。于是,譚知凡早年就跟著恩師學習殘貼制作。但每當問起師傅關鍵技術時,師傅總說:“你先去挑泥巴。”
于是,譚知凡又多了一項工作:挑土工。那時,建水城外有座滿目瘡痍的土山,由于經年累月的取土燒陶,早已不見半棵樹木。土山向陽坡、背陰坡,南坡北坡的土色截然不同,分別有白黃紫黑藍5色,是上乘的制陶用料。
在師傅授意下,年輕力壯的譚知凡挑著竹子編的土框,幾年間走遍了山里每一條溝溝,每一道坎坎,四處去挑土,一邊挑一邊琢磨各種土質的差異。隨著扁擔越磨越光滑,譚知凡對泥料的認識也越來越深,山里那個位置的土細膩,那個區域的土顆粒大,適合做哪一類的器皿,他都了然于胸。
幾年后,師傅才告訴他:殘貼制作最核心的秘密就是泥料的選擇和配比。泥料做得越細,配比越好,收縮率越大,殘片的可塑性也越高。他這才明白,師傅讓他挑了幾年土,就是要讓他從實踐中“挑出”殘貼制作的泥料選配這個“秘籍”。也從這時起,他深深地迷上了紫陶制作這門“泥巴匠”工作。
滄海桑田,多年過去了,廠子經歷了倒閉,撤銷,重組等一系列改革和變故。當年一同進廠的50多名工友,早已走的走、散的散,譚知凡卻始終堅持了下來,直到2005年退休。退休后,他一門心思鉆進了殘貼的制作和創新中,使得制作技藝更加爐火純青。一個器皿上,別人只能做一兩個殘貼,他可以制作出四五個塊面,還可以加上大量填刻。別人只能做出一幅畫的兩三個局部,他卻能通過特殊的泥料配比,將各個局部顯示在一個瓶上,產生了極高技術價值……2007年他的殘貼作品《扁天球瓶》獲“中國創造·民間文化品牌珍貴藝術品”獎,同年又獲得云南省首屆“工美杯”精品博覽會金獎;2009年,作品《華夏永聯》在第十屆中國工藝美術大師作品國際藝術精品博覽會獲銅獎;2011年8月作品《般若樽》獲云南省第五屆工美杯金獎;2014年作品《無相尊》獲全國百花杯金獎